正规的股票场外配资平台 构建企业主导型技能强企联合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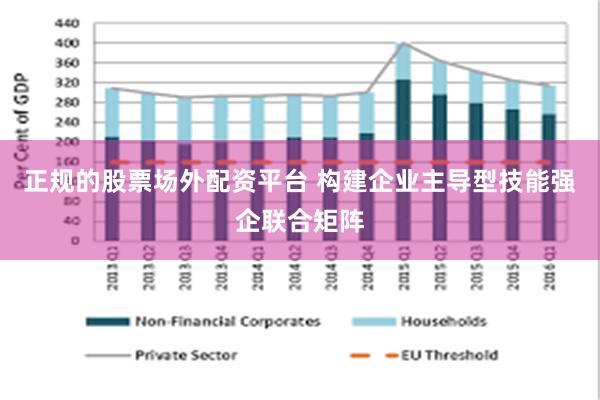
为对接和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和《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正规的股票场外配资平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日前发布了《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在明确企业对技能人才培养发挥主体作用的基础上,《指导意见》还就如何调动多元市场力量以扩大企业技能人才供给,以及完善企业技能人才的评价与激励体系等重要现实问题,给出了清晰的政策创新路径。因此,从精准意义上理解,《指导意见》所强调的“技能强企”就是“技能人才强企”。
企业技能人才大致可分为初级技能人才、中级技能人才与高级技能人才三类。初级技能人才包括学徒工、初级工两类,是能够掌握熟练技术并从事熟练劳动的从业者;中级技能人才包括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三类,除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以及具备较为精湛的操作技能外,他们还能在本岗位开展专利发明等必要的技术创新;高级技能人才除具有初中级技能人才的通用能力外,其在本岗位核心业务上大多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并能跨岗位展开协同创新,同时在创新链、产业链联合攻关中发挥重要作用,相应的创新成果既能解决关键技术与工艺操作瓶颈,更能破解“卡脖子”难题,这类人才主要包括高级技师、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三类。
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然而,不仅总量不足,占比也较低,同时结构性短缺现象更为严重。以制造业为例,到2025年,十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高达3000万人。在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制造业相关技术工种占据了58个。尽管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与德国、日本制造业45%—50%的技能人才占比相比,我国技能人才占比不到30%,高技能人才占比更低。不仅如此,数控、模具、仪表、电子电工以及焊接等工种的技能人才供给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且供需缺口仍在不断扩大。
技能人才的短缺不仅导致制造业效率长期低下,还使得企业许多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得不到及时的利用与维护,人机难以有效协同与匹配,企业难以形成必要的创新内驱力,最终直接延缓甚至阻碍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严重不足,势必弱化甚至阻断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的连接与共振,且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我国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以及未来产业布局的建设进程,进而增加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难度与风险。
基于技能人才缺乏的严峻形势,国家首先启动了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根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到2025年底,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要提升到30%以上。在此基础上,从2024年到2026年,全国要新培育领军人才1.5万人次以上,带动新增高技能人才500万人次左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开展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根据《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力争到2035年,培养造就2000名左右大国工匠、10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并以大国工匠和各级工匠人才为引领,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不仅如此,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高技能人才与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以及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一起被定义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这意味着从初级技能人才、中级技能人才到高级技能人才,再到技能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政策层面完全打通了企业技能人才成长的上升通道。而本次《指导意见》提出技能强企,其实就是对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的一次基础性夯实。
相比高等学校、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校)和培训机构等技能人才培养阵地,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企业不仅拥有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师傅)力量,还具备完整的生产车间、机械设备等硬件优势,同时学员从主观学习到能动应用的路径较短,总体培养成本较低,见效更快。正因如此,企业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除了常见的短期培训、技术比武、技能竞赛以及以小组或车间为单位的生产工艺与科技攻关外,按照《指导意见》,企业更要充分发挥以师带徒的作用,特别是利用技能大师工作室、劳模工匠创新室等特定机构的优势,统筹利用多渠道资金资源,建设技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与此同时,企业可以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场地和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联合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还可依托职业学校、企业培训中心等建设工匠学院。
为支持企业培养贴合岗位需求的技能人才,满足转型升级需要,《指导意见》提出,“支持企业按需设立学徒岗位,对新招用职工、在岗职工和转岗职工进行学徒培养”。同时,支持企业参与工学一体化、现场工程师培养,鼓励企业与学校联合,实现招工招生一体、入企入校同步、企校双师联合、工学交替培养学徒。就此,企业可将签订半年以上实习协议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毕业生)纳入新型学徒范围。对毕业后与实习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从入职开始由国家财政提供补贴。
与将企业作为技能人才培养主体相呼应,《指导意见》还提出了打造以企业为中心的“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具体而言,由企业出岗位、出标准、出师傅,学校出学生、出教师、出教学资源,政府出政策、出服务、出监管,形成以产业链链主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为核心主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培训机构、技能评价机构、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产业、教学、评价相互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
从“五级工”制度扩展到“新八级工”制度是我国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具体而言,在原有的初级工之下补设学徒工,在高级技师之后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由此形成了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的全新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因此,为策应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中的主体与中心角色,《指导意见》支持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对于解决重大工艺技术难题和重大质量问题、技术创新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师带徒效果明显的技能人才,可破格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同时,技能生态链链主企业可直接作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面向生态链内企业职工开展技能等级评价,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企业分配制度是吸纳、留住和激励技能人才的最重要风向标。除了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外,《指导意见》鼓励企业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以及急需紧缺的技能人才倾斜,并通过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合理确定技能人才的工资水平。尤其是对于高技能人才,《指导意见》提出要支持和引导企业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以及岗位分红、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办法,并要求国有企业在高技能人才中长期激励制度的创新方面发挥示范作用。除了薪酬物质激励外,《指导意见》还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企业技能人才的精神表彰。例如,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青年岗位能手等评选和荣誉要向企业一线高技能人才倾斜。同时,将企业急需紧缺的高技能人才纳入地方人才引进目录,并纳入城市直接落户范围。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被视为“国家的脊梁”、技术工人是一个家庭的骄傲完全不同,如今在不少人眼中,技工被视为“低人一等”的职业。不仅许多家长阻止孩子报考职业院校,而且孩子毕业后也倾向于“考公”“考研”,甚至更多青年人宁愿选择风里来、雨里去地当外卖骑手或网约车司机,也不愿意进工厂学技能与特长。技术工人被贴上了“差生”“无前途”等诸多负面标签。要扭转这种扭曲且不健康的认知与行为,除了继续通过媒体开展持续、大规模的正面引导与宣传外,各地还要通过打造人才港、工匠城等技能平台,设立技能展示、技能互动、职业体验区域,面向公众和青少年学生加强技能知识传播和文化培育。与此同时,更要大幅提升世界和全国各类职业技能大赛的含金量,企业也要加大对自身技术比武与技能竞赛的奖金支持力度。须知,在目前国内特殊的大众认知环境中,只有看得见、摸得着且足以令人心动的物质奖励,才是对技能人才的最好褒扬与宣传。
(作者为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正规的股票场外配资平台
